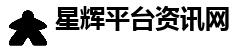夜半的城市像一只长睡的巨兽,呼吸在每条巷子里。窗外风声沿着空调的井道滑过,带着金属的潮湿和霉味。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,像被夜色抖醒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。屏幕亮起,显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:主人那家伙。短促的两声后,音量跌落成静默,像夜里的一次停电,让房间重新回到黑暗的重量。

我接起电话,听见对方的呼吸穿过线路,像雨点蹭在滑轮上,细碎而急促。声音低沉,带着陌生的嘶哑。他说今晚还在城里,像一只傍晚找不到路的猫,要我把握住某个时刻,别让光线吞没它。话语里还有一个名字,像一个旧伤口,在耳朵里微微刺痛。
电话里他谈起门铃的回响,露出旧日的影子:主人那家伙曾把秘密埋在角落,现在要把它翻出来。不是威胁,像一种冷静的要求,一种只有夜色才懂的语言。墙角的钟表跳动得很慢,仿佛在提醒我靠近的每一步都要算好方向。
街道像演奏厅,汽车的尾灯排成线,像红色的鱼在水里游。霓虹闪烁,墙面映出我的影子,跳动着不安的节拍。对话在耳朵中回放,像旧磁带的咔嚓声,指向一个模糊的地点。雨水沿着路面汇集,折成一条细细的光带,仿佛给今晚的任务找到了起点。
他提到那件事的名字时,心里一紧。声音里隐藏的承诺像一枚未扣的扣子,忽明忽暗。我没有立即答应,只让自己记住这条线索:钥匙、门、走廊尽头的光。夜风卷起湿润的纸屑,纸页在灯下发出微微的嘶响,像有人在翻阅我的过去。
午夜更深,城市的回声不肯安睡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,像风穿过铁门的回响。我把呼吸放慢,把手机合上。街灯把影子拉长再缩短,路面反射出水汽的光,像在指引我继续前行。城市继续呼吸,我的步伐也慢慢稳住,耳畔像回音的回音在心里层层叠叠。